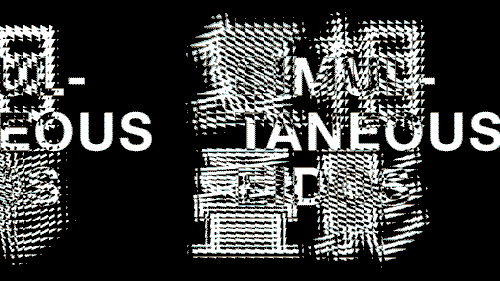
△ “复相·叠影——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主视觉
“复相·叠影——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即将在2017年12月15日至2018年3月8日在广东美术馆举办。在展览开幕之际,为加强学术交流、形成积极讨论氛围,广东美术馆在北京、上海、厦门及广州等多个城市举办流动学术对谈,邀请本次展览策展人、观察评论员、参展艺术家以及学术界人士共同参与主题讨论。11月11日下午,“复相·叠影——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流动学术对谈第一站在三影堂厦门摄影艺术中心举行,对谈主题为“影像艺术与在地文化”。
此次对谈由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美术馆馆长、“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总策划王绍强担任学术主持,“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观察评论员陈伟担任对谈主持。摄影艺术家、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联合创始人、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联合发起人荣荣,摄影艺术家、策展人、“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策展人曾翰以及摄影艺术家郭国柱参与对谈。本次流动学术对谈分为议题介绍、提问对谈以及观众互动三个部分。以下是对本次对谈的节选记录。
此次对谈由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美术馆馆长、“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总策划王绍强担任学术主持,“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观察评论员陈伟担任对谈主持。摄影艺术家、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联合创始人、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联合发起人荣荣,摄影艺术家、策展人、“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策展人曾翰以及摄影艺术家郭国柱参与对谈。本次流动学术对谈分为议题介绍、提问对谈以及观众互动三个部分。以下是对本次对谈的节选记录。

△ 对谈现场
陈伟:大家下午好!谢谢广东美术馆的邀请和三影堂厦门摄影艺术中心的支持;谢谢各位嘉宾和观众的到来。非常荣幸受邀担任本场对谈的主持,现在先由我介绍一下本场对谈的议题:“影像艺术与在地文化”。我们知道,人的大脑中大约有80%的认知和记忆都来源于眼睛对外部信息的获取和处理。可以说,我们在很多时候都生活在一个基于观看的影像世界里。这些影像或是对周遭现实的记录,或是个人内心的显影;它可能是在某个时空节点上看到的某个真相,也可能是在向我们打开一个可视物背后的未被言说的故事。在影像认知或建构中,我们发现,当代影像世界中杂糅着个体记忆、社会景观以及历史人文等各种层次复杂的信息与编码。
本次厦门站的对谈主题选定为“影像艺术与在地文化”,是希望借由影像的视角,参与到在地文化现象的思考及讨论中,以此拓展或延伸我们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认知和理解,以及文化与社会现实、艺术与个体内在的联系。本期议题也将结合广州影像三年展“特别展”与粤港澳地区影像脉络、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与厦门区域文化生态等具体案例展开互动分享。

△ “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观察评论员陈伟向观众介绍对谈主题
接下来,我想就以上议题思路和三位嘉宾一起交流探讨。广东美术馆作为国内较早关注和收藏摄影/影像艺术的公立美术馆,策划过很多国内外高水平的摄影展览及学术活动,并创立了自主品牌项目“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现更名为广州影像三年展),每届确立一个主题,清晰的学术定位,严谨的理论梳理,展现了不同时期的摄影实践。我们知道本次“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选定了“复相·叠影”(Simultaneous Eidos)作为主题,想请本届广州影像三年展策展人曾翰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策展团队为何选定这一概念?观众应该如何解读?
曾翰:近几年,无论是摄影的整体面貌还是影像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全面普及,给人们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对图片、影像感知方式的改变。现在人际关系的交往大多是通过影像完成,比如我们每天打开朋友圈、微博,会发现都是以影像为主,文字都是非常短的,图像在阅读信息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现在新型的人际关系已充斥了大量的图际关系,我们看到所谓的真实,都是通过影像视觉去感知。所以我们在探讨摄影时,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只讨论摄影的内容,而是要去讨论影像在当下的生发、生产机制或者对世界所带来的改变等等。
基于这样的背景,在策展工作会议上,策展人、学术委员和专家讨论出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词,那就是“复相”。“复”是重复、多重的意思;而“相”表达的就是客观世界外在的表现。后来我们又加上了“叠影”二字,表示当今人们的生活被各种影像交叉、重叠、缠绕的现象。

△ 摄影艺术家、策展人、“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策展人曾翰发言
陈伟:谢谢曾翰老师的分享。可以说,媒介语言的转向、传播方式的变化以及视觉观念的生成与美术馆、文化机构、策展人、艺术家以及公众认知程度有着诸多的关系。荣荣老师曾以艺术家的身份参加了2009年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而成立于2007年的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对于中国当代影像艺术的建构和发展更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推动作用。接下来,我想请荣荣老师与我们分享一下三影堂这十年来的探索和实践。
荣荣:我个人的经历可能很多人也有所了解。1993年,我带着一台相机到了北京。那时候我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虽然不知道能不能靠摄影养活自己,但因为还年轻,所以带着一种理想主义就开始艺术之旅。在那个时候,我拍摄了很多北漂的艺术家,包括在北京东村的那部分。大概经过了八到十年,在2000年后,我的作品开始进入国际视野。
早期摄影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因为摄影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艺术载体。大家一谈及摄影,就说我们是“搞照相的”。我觉得,中国有很好的摄影家,但是中国摄影家经常没有“家”。
三影堂的创立始于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梦想,就是希望和大家分享摄影。我认为摄影是透过相机将世界和人摄取到内心的过程,所以当有一天我们拍摄了足够多的东西,我觉得就有必要呈现出来。这和我选择成为摄影艺术家时的初衷是一样的,摄影是我与人交流的工具和方式,我的初心就是希望与更多的人分享我的创作、我的灵感。
我们之前到许多发达国家的美术馆参观时,发现他们有着很好的馆藏,但却很少看到中国摄影。所以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品牌的成立,可以说是填补了中国摄影的一部分空白,给摄影家提供分享和交流的平台,以个人微小的声音发出了对当下的思考。三影堂走过十年,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们大部分的展览项目都是跟国际接轨的,和欧洲、美国许多艺术机构、策展人、艺术家都有着很好的交流。
三影堂能一直办到现在,其实也是符合了当下时代的需求。影像在中国的发展还只是刚刚起步,未来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基础工作,通过传播影像加强人们对于影像的认知。

△ 摄影艺术家、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联合创始人、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联合发起人荣荣(右)发言
陈伟:谢谢。从荣荣老师的分享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影堂一直以来对影像艺术和文化建构的态度。您曾说过,关于摄影声音的转变不只是快门声音的转变,而是影像跟社会关系的转变。您是如何理解影像和社会及观众之间的关系?
荣荣:这好像是一个哲学性的问题。作为艺术家,我认为直觉对我来说很重要,就像我当初决定创办三影堂一样。作为艺术家,我觉得不能一直重复做某样事情,而必须对自己有一种挑战。成立三影堂的初衷,就是希望有一个属于摄影的独立空间。当观众进入到这个空间,就能被吸引到一个与现实生活有距离的时空里。很多人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北京的三影堂开在那么偏远的地方,我总是回答因为所有好找的地方都是商业空间,而我希望大家到三影堂是会静下心来看摄影,影像在这样一个空间中是“活的”。
摄影都是活在当下,在三影堂,大家不但可以看作品,还能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和艺术家交流,这就拉近了距离。以前我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但是做了三影堂后,因为需要传播,所以我就得学会与人交流。其实正是因为交流,图像与社会、公众才逐渐产生了涟漪。我希望厦门的三影堂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并逐渐跟周边融合成一个生态圈。
陈伟:谢谢荣荣老师的分享。影像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互生互为、相互交织。我们生活在一个影像世界里,从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闭上眼睛,所看到的现实影像都是彼此关联的连续的视觉流。在这样一个影像世界里,所有我们接收的影像信息都会以不同程度转入大脑,在记忆或认知的过程中,这些影像又转化为深度记忆和认知生产的一部分,如此循环。
“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的特别展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展览。这个展览主要的思路是从粤语(Cantonese)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对粤港澳的影像记忆进行梳理,并把艺术与社会、历史及人文间的关系串联在一起。下面我想请这个展览的策展人曾翰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策展思路,以及您是如何考虑区域的社会记忆和影像图层间的关系?
曾翰:“镜像粤影”是我为“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策划的特别展,内容是关于平行于全球化历史的珠三角摄影流变。题目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镜像”,表达的是摄影构成的历史和真实历史之间所形成的镜像关系,这也是我这部分展览的出发点。另一个是“粤影”,其实之前曾想过好几种说法,比如用“广州摄影”或者“珠三角”这些区域地理上的概念,但后来觉得“粤影”更符合地缘文化的分类。因为粤语不但包括了广东珠三角地区,也包含了香港、澳门地区的居民以及最早从粤语区移民到海外的华侨。再加上摄影在中国的登陆也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所以展览讨论的就是全球化历史中的珠三角摄影流变。

△“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 流动学术对谈·厦门站”现场
摄影是视觉现代化的象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珠三角地区是中国视觉现代化起源的实验场。珠三角地区是历史上不可忽视的区域。从广州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探索阵地;到1949年后,在当时的环境下,香港和澳门成为了中国与西方世界联系的前沿窗口;而改革开放之后,珠三角地区转为了世界工厂,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实验地。所以说,珠三角地区为全球化历史的演变提供了非常典型的案例和切片。
强调珠三角作为原点,并非一种自我加冕,而是忠于历史情境的思考。从历史语境上讲,很多中国摄影的“第一次”都是发生在珠三角地区。如:第一次中国报道有关于摄影的新闻,是1839年澳门的英文报纸《广州周报》(Canton Press)转载的一篇参观达盖尔工作室及观看银板照片经历的新闻;中国第一个自制照相机,并创造“摄影”一词的中国人,是广东南海人邹伯奇,他被称为中国摄影之父。他所撰写的《摄影之器记》,第一次出现“摄影”两字,后来这个词成为了对摄影约定俗成的翻译;1845年,美国人乔治·韦斯特(George West)成为了第一个在中国开设照相馆的人,他在香港开办了一家达盖尔银版商业照相馆;1858年,瑞士人皮埃尔·罗西耶(Pierre Rossier)在香港、广东拍摄了一批立体照片,并于次年公开发表,这批照片成为了第一批在西方公开发表的商业性质的中国照片;在1904年的一则广告里阿芳照相馆称,广东高明人黎阿芳(Lai Afong)于1859年创办了照相馆,这也是有记录以来第一个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在那个时候,中国最早开照相馆的都是广东人,七十年代后就形成了广东效应,在广东市场饱和后,照相馆就慢慢开到了内地,很多内地人也都跑到广东来学习。还有,中国第一批职业摄影者和第一批职业摄影传播者也都是广东人。而说到关于中国的最早一批摄影理论专著,也都是在广东出版的,包括邹伯奇的《摄影之器记》《格术补》,还有周耀光《实用映相学》,都些是中国早期摄影的重要著作。

△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1844年拍摄澳门的银版照片,是现存最早关于中国的照片
通过梳理,我们会发现珠三角的摄影史就是全球历史断代史的影像切片。上述提到的历史背景构成了策划这部分展览的前提。从1844年到现在,因为有太多史料和摄影作品,所以我在每段时期挑选了一组摄影师作为镜像案例去呈现。通过展览的呈现,我希望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摄影是如何独立于客观世界而自成一个世界,就像一个平行世界一样。通过对珠三角摄影案例的研究,我们希望能研究这种自我构建系统。

△ 陈劭雄,《街景-海珠广场》,摄影,128cm×85cm ,1999年
这次的特别展,我认为可以形成对摄影研究方法的讨论。在这个展览中,除了作品,还会展出大量的文献,包括视频、互动装置等。我并不希望只给大家看老照片,而是希望观众能进入到沉浸式的观展体验中,感知摄影师是如何构建起这个世界的。
陈伟:谢谢曾翰老师的分享。可以看得出来曾老师为这个展览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介绍,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一条平行于粤港澳真实历史的影像脉络。我们知道,厦门离粤港澳地区很近,在地缘文化、语言特征及生活习俗等方面有着许多的联系;而这座南方岛屿也正在快速地转向一座当代都市。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这一变化的亲历者,摄影艺术家郭国柱老师也是其中一位。他从个体经历出发、思考、观看,呈现了影像艺术与在地文化的另一面。接下来想请郭国柱先生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目前正在拍摄的系列作品《城岭》的创作以及相关的思考?
郭国柱:我在农村出生长大,2005年来到厦门。作为城市化的亲历者,我从农村基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所组成的熟人社会,进入非熟人社会,我必须调整我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关系。经过这些年的成长,我想用摄影来观察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 摄影艺术家郭国柱(右)介绍作品
《城岭》这个项目从2013年开始拍的,在这之前我一直关注城市化这一话题,但是没有找到较为合适的切入点。直到2012年到绍兴参与当地两本乡镇杂志采编工作,这两本杂志广泛讨论乡镇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问题,使我可以站在农村角度思考城市化的议题,于是开始筹划拍摄这个项目。
《城岭》以城市化过程中消失的乡村为线索,包括《流园》《堂前间》《遗物》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流园》,拍摄的是因为城市化而被荒废的村子,从城市的对立面农村,描绘当下的城市化进程,通过记录被遗弃的村庄景观,对农村的边缘性进行探讨。这一部分的拍摄还未完成,目前拍了广东、福建和浙江几个省份。
第二部分是《堂前间》,拍摄于杭州下属的新湾镇就地城市化过程中的大面积拆迁。堂前间是乡村自建房的一楼客厅的说法,这里是张挂招贴、平日接待乡里亲朋和年节团聚的重要场所,也是一个维系熟人社会中血缘和伦理关系的记忆空间。但随着他们迁到城市后,原有的熟人社会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
第三部分是《遗物》,这部分对村民所背离的原有生活场所、物品进行肖像式拍摄,窥探他们旧时生活的内在记忆与体验。这就是我作为城市化的亲历者,从农村到城市,再来观看城市化进程所拍摄的影像。

△ 郭国柱,《流园》No.01|122°82′E 30°72′N,2015年-至今

△ 郭国柱,《堂前间》No.21,2013-2014年

△ 郭国柱,《遗物》No.17,2013-2014年
陈伟:谢谢国柱老师的分享。我们知道在当代影像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个是影像生产者(IMAGE MAKER), 另外一个就是影像编辑者(IMAGE TAKER)。我想请荣荣老师从艺术机构创办人的角度谈谈,您是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展览或项目的?
荣荣:三影堂毕竟是私人创办的机构,所以对艺术家或作品的选择肯定包含了自己的偏好。至于三影堂项目的选择,就拿我们从2009年开始举办的“三影堂摄影奖TSPA”为例,启动这个项目是希望给年轻人提供一个展示的空间。因为当时国内没有太多摄影类奖项,“三影堂摄影奖”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刚才曾翰老师讲的“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的特别展“镜像粤影”,将从珠三角100多年的摄影史梳理了出来并形成脉络,我十分欣赏。因为直到现在,中国的摄影史还多是国外专家在撰写,我们看不清楚中国城市和人文的发展。我认为我们可能忽略了影像的重要性,并没有意识到影像可以见证的社会发展。
视觉这个语言其实非常重要,我们每天看影像,但我们却读不懂它。我认为我们需要静下来审视和研究影像,并让年轻人参与到对影像的讨论中,这是作为艺术中心的责任,也是美术馆应有的担当。
对我来说,三影堂未来的发展有着无限的可能,也充满了未知的挑战。我希望交给更专业的人去挖掘更多有潜力的年轻一代,而不只以我个人的偏好来选择。随着三影堂越来越成熟,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可能性。

△ 现场嘉宾对谈互动
陈伟:谢谢荣荣老师的分享。想请曾翰老师从策展人的身份,谈谈您是如何选择参展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
曾翰:首先我要说,其实我不是一个专业策展人,我是一名摄影师。一开始策展其实是出于热爱和喜好,当我从美国学习回来后,我觉得策展对于我来说变成了一种研究方法,甚至变成重新创作的方式。
2010年广州时代美术馆刚开馆时,我为其策划了第一个展览,叫“中国景CHINESCAPE 中国当代景观摄影联展”,策划这个展览就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在做景观摄影,也关注景观摄影在中国的发展,包括外国人是如何观看中国,所以那次展览我挑选了五位西方摄影家和六位中国摄影家来拍摄中国的城市化景观,透过展览对景观摄影进行研究。
“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的特别展“镜像粤影”其实是一个我多年前就想研究的课题,这次终于得以实现。今年我花了大半年时间对展览进行调查和研究准备,收获良多,因为我不是做摄影史出身,对摄影史有很多不了解,很多时候做事都是凭直觉。这次研究让我补了很多课,让我更加了解摄影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我以后会更偏向于做研究型的展览,因为我觉得中国这类型的展览还是比较少。三影堂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典范,他们一直在做摄影研究方面的收藏、出版和展览,这是中国特别需要的,而不是只做让大家凑热闹的展览。
陈伟:我们再换一个角度,三位嘉宾都是国内外非常活跃的摄影艺术家,或者说是影像生产者(IMAGE MAKER),有一个看似具体但又十分抽象的问题,那就是当你们拍照的时候你们在想什么?
荣荣:拍照就拍照按下快门,什么都不用想。
郭国柱:摄影比较依赖于现实世界,所以我会用它观察我所亲历的事情,或者我所关心的事情。比如我正在进行的城市化项目,是因为我在来厦门工作以后,各种现实的问题扑面而来,很大程度上影响或者改变了我,这些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和现实面对,我就会考虑用摄影的方式观察它,或把它纳入我的生活中。我在厦门生活几年以后,因为家里面老是在问什么时候买房子,问多了我就被带进去了,所以我就会开始观察这个事情,后来有了孩子就面临教育资源问题,以及父母开始变老,又操心医疗资源等等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扑面而来的时候,自然被带入。
曾翰:这个问题说起来太庞大了,荣荣老师非常聪明,一句话就概括了。
我少年时期想做一个文学青年,到了大学就开始自学摄影,觉得摄影更符合我的表达。后来我发现,拍照跟文学里表达的东西是一样的,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作家是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我觉得我作品里表达的中国现实就是卡夫卡里的现实。我们看卡夫卡的文字世界是非常荒诞或者超现实的,但是他写的其实都是最真实的现实。
对我来说,拍照有时候是靠直觉,有时候是因为受到外部世界刺激,又或者被自身经历、成长、情感和各方面问题压迫,让我不得不用摄影表达。而最近几年我特别喜欢用摄影构建一个自我的世界,其实荣荣老师也是在用摄影构建自我的世界,这是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属于自己的小宇宙。这是摄影最吸引我的地方。
荣荣:我再补充一下。当初拍照是因为不拍照就觉得浑身不舒服,拍完之后人就变的非常舒服,感觉很多东西都释放了出来。现在如果问我为什么少拍照了,是因为现在想得太多。所以说摄影还是要拎起你的工具走出门,要直接了当,并在过程中重视当下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荣荣:我再补充一下。当初拍照是因为不拍照就觉得浑身不舒服,拍完之后人就变的非常舒服,感觉很多东西都释放了出来。现在如果问我为什么少拍照了,是因为现在想得太多。所以说摄影还是要拎起你的工具走出门,要直接了当,并在过程中重视当下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陈伟:谢谢三位老师的分享。从广东美术馆的“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谈到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的探索与实践,从社会记忆到影像图层再到在地文化,我们希望有更深入的讨论,听到不同的声音和解读,现在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座的各位:
观众提问: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刚才的分享,受益匪浅。我自己很想成为专业的影像批评人,但从旁人角度觉得做这个就会活不下去。不知道您几位对有志于从事影像批评研究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 观众提问互动
荣荣:关于摄影批评,一定要跟上国际的步伐。年轻人应该更关注当下的影像,要在这个行业有所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国际的动向,这样才能从自己的角度提出属于自己的问题。
曾翰:其实你刚才讲的问题在很多艺术创作或艺术研究领域都存在着。即便我们生活在一个商业社会,许多东西都是不能马上变现,让人马上能活得很好的。但是没有办法,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想要继续走下去就要想别的办法赚钱。不管对创作者或理论者来说,现在比起以前还是多了许多平台,比如现在有着各种各样的基金可以支持创作者或理论者的工作。
观众提问:各位老师好,现在有许多摄影师在尝试对作品做一些二次创作。请问四位老师对于这种二次创作有什么看法?
荣荣:无论是什么创作方式都是非常好的,因为摄影也是包括后期制作、二次创作,很多艺术大师都用电脑做二次创作。最重要是你想要表达什么,至于过程怎么做都是没有限定的。
曾翰:二次创作没问题,但是我有一个疑虑,就是当越来越多人只是拿到一个影像,再通过这个影像进行创作时,我们有多少人在关注真正的现实?这值得我们去思考。
作为我们这一代的摄影人,我很欣赏郭国柱,因为他的摄影是面对的,是真正的现实。他去拍一个村子,村子没有路,车也开不进去,他就背着很重的相机走进荒芜人烟的地方去拍照。如果别人将这些作品再拿过来二次创作,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有志从事摄影这个行业,一定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郭国柱:关于二次创作,我持比较包容的态度,甚至对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想法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多样化以及对于影像边界的探索是很好的事情。
陈伟:无论是绘画还是传统摄影都还留有原作或底片的概念;但在今天,我们每天面对着如此多的数字影像,我们可能需要思考影像到底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关于影像,以及影像之后的影像,也是从绘画到摄影再到虚拟现实一直以来我们在讨论的话题,我们可以用一个相对开放的态度面对影像生产、视觉观念的变化中产生的诸多疑问和可能性。

△ “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 流动学术对谈·厦门站”现场

△ “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 流动学术对谈·厦门站”
嘉宾与工作人员合影
文&图 / 吴俊贤
(部分图片由三影堂提供)
编辑 / 刘丹妮




